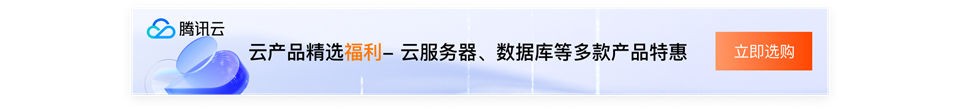初冬的筑城,,夜色闌珊之時(shí)街上行人已稀,小十字附近的一條背街巷口,,還有幾位推著板車的叫賣人:“新鮮現(xiàn)炒的糖苞谷花,,兩塊錢一包咯!”
“吃粗糧對身體好啊,,幫助消化的,,我這個(gè)苞谷花不含鉛。”見記者走過去,,賣苞谷花的中年男子趕緊介紹,。男子滿面煙塵,衣衫單薄,,雙手漆黑,,一口牙齒被反襯得雪白。板車上,,除了炒好待賣的苞谷花,,還有一架舊式黑色瓦炒鍋,、鼓風(fēng)機(jī)、備用煤料及高壓鍋,。兒時(shí)排隊(duì)打苞谷花的記憶開始浮現(xiàn)腦際:一位扛著葫蘆一樣黑鍋的老人,,將苞谷變成了金黃色的爆米花,老人是那時(shí)最受歡迎的“魔術(shù)師”,。
“70年代我還是個(gè)娃娃的時(shí)候,,都是些四川人擔(dān)著炒擔(dān)來村頭加工苞谷花,哪家需要炒的,,就提上苞谷去排隊(duì),,幾毛錢就可以炒上一鍋,”這位叫游仁民的炒苞谷花人來自綏陽縣,,他回憶,,“那個(gè)時(shí)候,最高興的還是娃娃,,圍在旁邊,,等著‘轟'的一聲響,,沖到熱氣騰騰的篾筐邊搶上一把就跑,。”在那個(gè)物質(zhì)生活相對貧乏的年代,吃苞谷花還算是奢侈的享受,,一般只有逢年過節(jié)的時(shí)候,,各家才會(huì)舍得拿出幾斤攢下的苞谷子來炒。過年走家竄戶拜年時(shí),,主人會(huì)捧上一捧,,炕在火爐邊,當(dāng)作一種款待,。那些圍坐在爐邊嚼著香脆苞谷花的日子,,顯得格外溫馨。
“經(jīng)常圍在一旁看,,慢慢地對怎么加工也知曉一二了,,后來干脆也買回一套設(shè)備,學(xué)著外地人的樣子,,在村頭炒了起來,。”游仁民說。上世紀(jì)70年代末,,各家并不富裕,,平日里炒苞谷花的人很少,掙不了什么錢,。于是游仁民就農(nóng)忙時(shí)種莊稼,,閑時(shí)才會(huì)在村頭架上炒鍋,。
“那時(shí)候,一般都是自家?guī)г?,像苞谷,、糖精、豬油,,要是嫌麻煩了,,也可以在我這里買。臘月20到過年那段時(shí)間,,是生意最好的時(shí)候,。后來我想,城里頭的需求量肯定大些,,就干脆到縣城里趕場,,有時(shí)1天能掙個(gè)10塊、20塊的,。”游仁民告訴記者,,上世紀(jì)80年代中后期,炒苞谷花也開始向縣城轉(zhuǎn)移發(fā)展,。
“我同村的一個(gè)老鄉(xiāng),,上世紀(jì)80年代末到貴陽一家苞谷花廠打工,活路累,,掙錢還少,,一氣之下,他辭工出來自炒自賣,,生意居然還不賴,。老鄉(xiāng)回去提到這事時(shí),我也動(dòng)了心:干嘛不去省城試一下呢,?”講起來筑的緣由,,游仁民顯得有些激動(dòng)。那是1994年,。
據(jù)游仁民介紹,,剛來筑城時(shí),不敢在街頭擺炒攤,,他便在煤礦村附近租了一間小屋,,在家炒好后,再拿到街上叫賣:“當(dāng)時(shí)去得最多的是市西路,,可以在眾多的店面里推銷,。5角錢一包的苞谷花,連本帶利,,平均1天可以賣上30元到40元,。”
“剛開始,,因家里的農(nóng)活丟不下,春天到夏天我一般都回家種地,,9月份到次年苞谷花生意好做的時(shí)候,,才來貴陽炒苞谷花。后來我發(fā)現(xiàn),,炒苞谷花賣比種田收入多,,就干脆把農(nóng)田租出去,帶上老婆娃娃,,一起來貴陽,,靠炒賣苞谷花為生。”說這話時(shí),,游仁民臉上寫滿了創(chuàng)業(yè)的激情,。
“從1998年起,我開始嘗試推著板車出來邊炒邊賣,,就像現(xiàn)在這樣,,”游仁民扶了扶板車把手,“這車一直跟著我,,有10來年了呢,。”游仁民介紹,90年代末期,,一個(gè)介紹一個(gè),,來貴陽炒苞谷花的鄉(xiāng)里人越來越多,,形成了一個(gè)龐大陣營,。
2002年以后,炒苞谷花的品種有了改良,,從原來單純的粗苞谷花,,漸漸發(fā)展到糖苞谷花、半花半啞苞谷花,、奶油苞谷花等多個(gè)品種,,而且葫蘆炒鍋的鍋口也不用鉛墊了。“別看我這套行頭簡陋,,可全是精心裝備的,,現(xiàn)在炒苞谷花哪有‘轟'的一聲啊,都改用排氣的方法了,。”游仁民指指板車上的麻袋和膠桶:“早就不用篾筐了,,這樣子也方便攜帶。”
“別看我這小小板車,,收入也夠一個(gè)家庭的開銷了,。”對于自己的職業(yè),,游仁民感到驕傲,“只要肯吃苦,,誰都可以自食其力,。”
深夜的筑城,寒意漸濃,,但這位炒苞谷花人的故事,,卻讓人心中生出幾分暖意。
“吃粗糧對身體好啊,,幫助消化的,,我這個(gè)苞谷花不含鉛。”見記者走過去,,賣苞谷花的中年男子趕緊介紹,。男子滿面煙塵,衣衫單薄,,雙手漆黑,,一口牙齒被反襯得雪白。板車上,,除了炒好待賣的苞谷花,,還有一架舊式黑色瓦炒鍋,、鼓風(fēng)機(jī)、備用煤料及高壓鍋,。兒時(shí)排隊(duì)打苞谷花的記憶開始浮現(xiàn)腦際:一位扛著葫蘆一樣黑鍋的老人,,將苞谷變成了金黃色的爆米花,老人是那時(shí)最受歡迎的“魔術(shù)師”,。
“70年代我還是個(gè)娃娃的時(shí)候,,都是些四川人擔(dān)著炒擔(dān)來村頭加工苞谷花,哪家需要炒的,,就提上苞谷去排隊(duì),,幾毛錢就可以炒上一鍋,”這位叫游仁民的炒苞谷花人來自綏陽縣,,他回憶,,“那個(gè)時(shí)候,最高興的還是娃娃,,圍在旁邊,,等著‘轟'的一聲響,,沖到熱氣騰騰的篾筐邊搶上一把就跑,。”在那個(gè)物質(zhì)生活相對貧乏的年代,吃苞谷花還算是奢侈的享受,,一般只有逢年過節(jié)的時(shí)候,,各家才會(huì)舍得拿出幾斤攢下的苞谷子來炒。過年走家竄戶拜年時(shí),,主人會(huì)捧上一捧,,炕在火爐邊,當(dāng)作一種款待,。那些圍坐在爐邊嚼著香脆苞谷花的日子,,顯得格外溫馨。
“經(jīng)常圍在一旁看,,慢慢地對怎么加工也知曉一二了,,后來干脆也買回一套設(shè)備,學(xué)著外地人的樣子,,在村頭炒了起來,。”游仁民說。上世紀(jì)70年代末,,各家并不富裕,,平日里炒苞谷花的人很少,掙不了什么錢,。于是游仁民就農(nóng)忙時(shí)種莊稼,,閑時(shí)才會(huì)在村頭架上炒鍋,。
“那時(shí)候,一般都是自家?guī)г?,像苞谷,、糖精、豬油,,要是嫌麻煩了,,也可以在我這里買。臘月20到過年那段時(shí)間,,是生意最好的時(shí)候,。后來我想,城里頭的需求量肯定大些,,就干脆到縣城里趕場,,有時(shí)1天能掙個(gè)10塊、20塊的,。”游仁民告訴記者,,上世紀(jì)80年代中后期,炒苞谷花也開始向縣城轉(zhuǎn)移發(fā)展,。
“我同村的一個(gè)老鄉(xiāng),,上世紀(jì)80年代末到貴陽一家苞谷花廠打工,活路累,,掙錢還少,,一氣之下,他辭工出來自炒自賣,,生意居然還不賴,。老鄉(xiāng)回去提到這事時(shí),我也動(dòng)了心:干嘛不去省城試一下呢,?”講起來筑的緣由,,游仁民顯得有些激動(dòng)。那是1994年,。
據(jù)游仁民介紹,,剛來筑城時(shí),不敢在街頭擺炒攤,,他便在煤礦村附近租了一間小屋,,在家炒好后,再拿到街上叫賣:“當(dāng)時(shí)去得最多的是市西路,,可以在眾多的店面里推銷,。5角錢一包的苞谷花,連本帶利,,平均1天可以賣上30元到40元,。”
“剛開始,,因家里的農(nóng)活丟不下,春天到夏天我一般都回家種地,,9月份到次年苞谷花生意好做的時(shí)候,,才來貴陽炒苞谷花。后來我發(fā)現(xiàn),,炒苞谷花賣比種田收入多,,就干脆把農(nóng)田租出去,帶上老婆娃娃,,一起來貴陽,,靠炒賣苞谷花為生。”說這話時(shí),,游仁民臉上寫滿了創(chuàng)業(yè)的激情,。
“從1998年起,我開始嘗試推著板車出來邊炒邊賣,,就像現(xiàn)在這樣,,”游仁民扶了扶板車把手,“這車一直跟著我,,有10來年了呢,。”游仁民介紹,90年代末期,,一個(gè)介紹一個(gè),,來貴陽炒苞谷花的鄉(xiāng)里人越來越多,,形成了一個(gè)龐大陣營,。
2002年以后,炒苞谷花的品種有了改良,,從原來單純的粗苞谷花,,漸漸發(fā)展到糖苞谷花、半花半啞苞谷花,、奶油苞谷花等多個(gè)品種,,而且葫蘆炒鍋的鍋口也不用鉛墊了。“別看我這套行頭簡陋,,可全是精心裝備的,,現(xiàn)在炒苞谷花哪有‘轟'的一聲啊,都改用排氣的方法了,。”游仁民指指板車上的麻袋和膠桶:“早就不用篾筐了,,這樣子也方便攜帶。”
“別看我這小小板車,,收入也夠一個(gè)家庭的開銷了,。”對于自己的職業(yè),,游仁民感到驕傲,“只要肯吃苦,,誰都可以自食其力,。”
深夜的筑城,寒意漸濃,,但這位炒苞谷花人的故事,,卻讓人心中生出幾分暖意。